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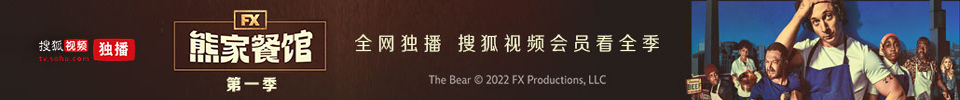
N个人收藏





盘腿炕上,工程兵连队的迎新晚会
发布时间:2024-11-23 浏览次数 :25
入伍后初次在军营过年,提前十几天,班长在班务会上宣布,连队要求年底的文艺活动以班为单位举行,在各班的炕头进行,每人都要有节目,多人联合的不受限制。
我们施工部队没有固定营房,好几年一直住自己搭建的土坯简易营房,用火墙、地火龙、火炕取暖。全班十余人住一间房子,进门就是双排炕,中间过道一米多。门外另外砌了一个简易门楼,有地炉子,以及木柴等。除了工地施工、操场练兵,许多班务活动就在炕头上了。军队的文化生活一直是很丰富的,连队基本每月一次晚会,歌曲、电影也比同时期的社会组织多许多。
班里“四位一体(班长、副班长、党员、团小组长碰头会)”开会商量办法,希望超过兄弟班,或者至少不能落后,分头发动。还把室内气氛布置一新,墙报更换成过节喜色,挂上了最新的毛主席像,学习园地上张贴着每个战士的最新学习体会。班长是吉林扶余县的老兵,几天前到当地农贸市场买到一斤烟叶子,福建安溪的战友打开了老家寄来的“土茶”,上海兵的大白兔奶糖也摆出来了。司务长与给养员到各班,分给我们炒熟的花生、葵花籽,还有北京出品的糖块。地炉子上煮着安溪土茶水。
宿舍里的被褥折叠的中规中矩。即使节假日,也不敢破坏它。这次晚会,要坐到炕上,我们把半页褥子掀起来,盖到四四方方的被子上。 炕是早上就开始烧的,炕面有点烫。南方兵开始不习惯:空气干燥、灰尘多、嗓子发干、炕头炕尾温度差异大。几年后体会,如果从寒冷潮湿的施工作业面下班,洗澡之后,躺到热炕头,非常解乏、解困!
室外传来哨音,值班排长口令:各班晚会开始!
连里干部分头到各班参加活动,蒋副指导员到我们班。晚会由班长主持。先挤挤的站在两排炕中间的过道,集体凝视毛主席像,背诵毛主席语录“老三段”。而后盘腿坐到自己铺位的芦苇席上。班长说,今天晚会,有舞蹈节目的,可以下炕在过道上,其余都坐在炕上。时间长了有人不习惯,可以适当伸开双腿,小幅度活动活动,但是注意不要把内务(部队有大内务、小内务,平时室内秩序可以说是小内务)整乱了。他让蒋指导员先表演一个,指导员说我先欣赏你们的。
泉州的陈战友文化比较高,朗诵一首自己写的颂扬领袖、表达自己保卫祖国决心的诗。安溪傅战友唱拿腔拿调,唱起了家乡小调。许多年后,才知道就是长盛不衰的《采茶舞曲》。东北籍老兵,在过道上,扭起吉林大秧歌。还有口琴、二胡、竹板等表演。我背诵了一曲东坡赤壁。蒋指导员用老家四川话说了一个讽刺解放前地主老财的幽默。大家都没有文艺细胞,也没有高档音响加持,但是,战友们都非常开心、投入。
司务长分过来的小食品,非常助兴。准备好的节目基本完成,慢慢就过渡到轻松聊天阶段。爱抽烟的三五人聚到一起,用手撕碎烟叶,放入扑克牌大小的白纸,卷成缩细了的粽子形状,他们说这就是“喇叭烟”,也有叫“蛤蟆烟”的。说城市人抽的烟两头一般粗,价钱贵,还不够味、不过瘾;他们还介绍,东北烟叶最好的是蛟河烟、漂河烟。傅战友平时很少与人交流,今天非常开心,讲了不少老家山上山下的趣事(后来别的福建战友说,他父亲早亡,单亲母亲拉扯长大;家在茶区,但没有自家的茶叶,他老妈寄来的茶,是十来元钱买的,花了几个月的生活费)。
室外又传来值班排长的哨音和通知:晚会结束,打扫卫生,准备开饭。今天晚饭——吃饺子!
后来,我还多次参与部队与驻地群众“双拥”活动,慰问当地优抚对象,坐到老乡炕头,嘘寒问暖,谈天说地。但每次时间不长,主要的是体现一种军民团结的气氛。至今回忆,还是自己连队、自己班里,炕头晚会,烟气缭绕、土里土气,官兵一致,暖意浓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