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墙,只有在北方使用,南方人是不知道的。我从大西北回到故乡已经30年了,在我记忆中,火墙的影子也越来越遥远。即使现在新疆兵团人,大多数都住进了楼房,火墙也只在连队部分老房子里面存在,也越来越看不见踪影。
火墙是在大西北冬天屋里取暖的必备设施,它是用土块垒的火炉与土块垒的空心墙以及伸出屋顶同样是土块垒的烟囱相连的供热系统。炉子里用煤炭生火,上面盖着一圈圈的炉盖,根据锅底的大小揭开不同的炉圈就可以烧水做饭。带有剩余热量的煤烟通过炉口进入空心火墙,这些热热的烟气从空心的火墙中被隔离的像迷宫一样的烟道里通过,烤热了薄薄的火墙墙身,把热量散发在屋子里,废烟则通过火墙上方的烟囱从屋顶排出到屋外。这是一种高效率利用热能的装置,如果打炉子火墙的师傅技艺高超,炉火烧起来特别利,火墙也特别抽风,那炉子与火墙烧起来呼呼的,有时候甚至可以将整个火墙烧得通红,晚上不用点灯都可以看清屋里的物件。
那时候,全连一排排低矮的土屋上,每间屋顶一个烟囱矗立着,每当夜幕降临,一个个烟囱相继冒出淡淡的烟雾,在月光与寒雪的交相辉映下,很有点梦幻般的色彩。
我们还是单身的时候,集体宿舍里就由连队派泥工师傅打好了火炉与火墙。年轻人大多比较懒,特别是男生。睡觉前架的一炉子火,呼呼地烧到大半夜就开始慢慢的烟熄火熄,那时候谁都不愿意从热被窝里爬出来往炉子里续点煤。冬夜漫长,往往到下半夜炉子里的火熄了,要不了多长时间屋子里就像冰窖一样,隔夜放的备用水都可以结一层厚厚的冰,那木板门缝里也都结上一溜溜冰霜甚至冰柱!每个露在被窝外面的头脸,自己呼出的热气都在胡子眉毛上结成白白的霜,一个个成了圣诞老人。
在火炉边烤鞋,在火墙上烤毡袜毛袜裹脚布是单身汉的习惯,白天别看冰天雪地的,但在挖大渠工地干起活来,胶靴里面的毡袜或者棉胶鞋里的毛袜裹脚布就会捂得脚上出汗,一天劳动下来,回到宿舍脱下鞋子,里面全都湿漉漉的,晚上必须烤干。冬天屋子封闭比较严实,窗子上都用报纸、塑料纸糊起来,有的甚至干脆用土块垒的严严实实的,那些臭袜子烤起来的气味,弥漫在整个房间,现代人不难想象那是何等的不堪。但一复一日,大家似乎习惯了那种味道,闻臭不臭了。有时候火墙烧得通红,往往出现棉胶鞋或者毡袜毛袜裹脚布烧着了的小事故,等到呛人的浓烟把一个个年轻人熏醒的时候,那些搁在炉子边上火墙顶部的脚上物件都变成一堆堆黢黑的焦炭。
单身汉都很羡慕别人小家户的生活,一间房子一小院,老婆娃娃小锅饭。进到人家屋里,那种温馨的气息扑面而来,日子过得那个润,足以让年轻的单身流出哈喇子。等到这些人成家之后,才感觉到柴米油盐的繁忙。就听到有位仁兄,下班后忙得稀里糊涂的,炉火正旺,锅里汤水滚滚,头上也渗出了热汗,老婆在炉边往锅里揪片子,老公将刚洗好的孩子尿布挂在火墙周围的铁丝上面,雾气弥漫整个房间,等到汤饭做好了,怎么就看见一张大面片浮在锅里,捞起来一看,尿布不知道什么时候掉进去和面片一起煮了起来。
冬季也是煤气中毒的高发季节。一个团场就是一个封闭型的小社会,一家有事,要不了多长时间全团都知道。也时常听说谁谁家的娃娃被煤气打死,谁谁的孩子被煤气熏成脑瘫,还有谁谁命大,觉得中煤气了,凭着强烈的求生欲望与顽强的生命毅力,硬是滚到床下,一步一步地爬到门口,就着门缝里进来的新鲜空气捡回一条命。
冬季连队里还有一道奇特的风景,那就是每天晚上的全连职工大会,或学习文件读报纸,或总结工作布置任务。全连几百号人全都集中在食堂里,中间置一用废旧汽油桶改装的火炉,炉膛里火焰熊熊,连烟气带火焰一股脑钻进硕大的火墙里,整个就像开火车似的轰隆隆地作响。人们围坐在周围全都不敢靠近,热辐射像烤馕似的炙着四周的人群。连队吃过晚饭,一个废弃的拖拉机链轮代替的钟敲响了,人们从各间低矮的屋里陆陆续续汇集到这里。一个个进来的人都径直走到他自己老蹲的角落,裹紧棉衣,低头不语地卷起莫和烟,满有滋味"吧吧"地吹着"烟囱"。一眼望去,浓浓的烟雾遮住台上用来照明的马灯,使整个场面显得幽深黑暗,根本看不清人的面孔,只有星星点点的烟头在各个角落忽闪忽闪。那些小媳妇老嫂子们,端来矮凳坐在上面,手上也没闲着,一根筷子戳进一个大洋芋里,就在能见度那么低的情况下,熟练地捻起了羊毛,不知道她们的耳朵听没听到连长指导员在上面讲的什么。
俱往矣,现在想看到这种场景,恐怕是不可能了。岁月犹如流水,无情地冲刷着大地,偶尔只留下一丝沧桑,斑驳地停留在某处不为人知的地方,赫然被人发现,令人怅然叹息。
火墙,也就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
当年挖大渠的场景
当年的营房
连队营房上清晰可见的烟囱
团部房屋上的烟囱
当年的连队
连队一隅,烟囱林立
当年兵团的学校
现在兵团人都住上了这样漂亮的楼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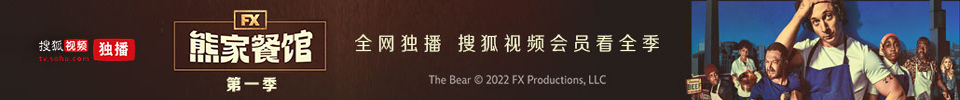
N个人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