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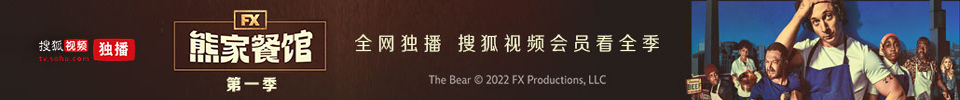
N个人收藏





难忘那儿时的“大炕”
发布时间:2024-11-13 浏览次数 :23
炕,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关于炕的文字记录,始于北魏时期。在乾隆年间,每逢过小年祭灶的时候,乾隆皇帝总会亲自进行一项独特的仪式:击鼓、拍板、唱曲儿,可见炕的文化意味深远,炕的乐趣其乐无穷。有人说,炕也可以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了!

炕,见证了祖辈勤劳朴素的生活。记忆中奶奶与母亲一有空就坐在炕上,一边聊着家长里短,一边做手工针线活:纳鞋底、纺线等等,我时常伴着”哧溜哧溜”的纳鞋底声或”嗡嗡嗡”的纺线声,进人甜美的梦乡。炕不仅给一家人营造了团聚、祥和、温馨的氛围,更使人咀嚼到家的味道,这的确是一种幸福难得的记忆。
我从小就和炕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炕,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人生的始发站,又是我幼小时期的欢乐天堂,更是我成长的摇篮。它见证了我儿时的成长岁月。时至今日,那宽大暖和的热炕,那浓郁的乡土乡情,还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那厚重的烟熏味、土腥味不但没有被时间稀释,反而更加历久弥新。那种幸福、苦涩、温暖的的味道让我永久留恋------
炕,承载了太多美好的往事。过去的年代里,无论谁家盖起了新房,庄乡爷们见了主人都会问一声:”炕盘了没有?”如果村里谁家娶来新媳妇,大家就会说:”新媳妇到炕上了”如果哪位老人患了重病生活不能自理,人们常常会同情地说:”某某瘫在炕上了”。

炕,是幸福的象征,民间流传着一句生动形象的顺口溜:“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便是最好的佐证。炕还是待客的礼节,家里来了客人,热情好客的主人往往会说:“上炕吧!”,这是农家一种最高规格的礼仪。
记得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冷。我放学后,把书包一扔,鞋一脱,跳上炕,全身立刻感到一种温暖,这温暖纯真、质朴、贴心。那苦乐相伴,充实盎然的日子里,洋溢着一家人太多的幸福和欢乐。母亲经常带我和妹妹去大娘家串门,坐在大娘的炕上,和大娘的孩子们一起听大娘讲故事。大娘是唐山人,她每年都要去唐山住上一段日子,回来就给我们讲在城里的所见所闻。城里人每天都能吃到香喷喷的肉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记得大娘讲得眉飞色舞,大家听得目瞪口呆、垂涎三尺的样子,当时我心中的羡慕之情无以言表。
由于大娘见广识多,又是那个年代很少见的文化人,她的故事里既有日月星辰雨,又有山水草木兽。听她讲故事就像看一幅幅画卷,翻动纸页时呼吸生动、满目新鲜。胡同里的大人孩子都愿意去她家里玩!在大娘家的炕上,我听过《白蛇传》、《女郎织女》、《狼外婆》、《神丫头》、《日本鬼子》等故事,大娘的炕以独有的文化氛围浸洇了我的整个人生,我后来的一切似乎都与这里有关。

我的中学阶段,正值上世纪70年代,那时候乡村里都是凹凸不平的土路,而且又缺乏交通工具,因此离学校5里地的学生都需住校。当时我们住在大程乡卢庄学校所在村老百姓家的土炕上,每人除了简单的被褥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生活用品。10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人均占炕大约30公分宽。晚上睡觉时,头朝外、脚朝里摆成一排,一个挨着一个,挤得严丝合缝,想翻个身就很困难。
有一个冬日的夜里,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当时农村还没有电照明,自己也没手电筒,就裹上棉袄摸黑去院子里的露天厕所。当打开那扇老式木门时,才发现天上静悄悄的下了一场大雪,目力所及处都是白茫茫一片。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院子西南角的厕所里走。路过厕所旁边的柴草棚子时,突然听到一阵语无伦次的的”嘿嘿”声,吓得我毛骨悚然,浑身是汗,困意全无。我壮着胆子仔细一看,是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正躺在柴草上自言自语呢。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当我从厕所急忙回到屋里时,我睡觉的地盘已被相邻的同学翻了个身占领了!看她睡得正香,我不忍心推开她,就只好蹲在炕边,披上衣服,等待她再翻过身去的一瞬间,再迅速躺下!不然位置又会被另一侧的同学占领。

虽然那时上学的“硬件”如此苍白,但浓厚的学习兴趣,刻苦的学习态度却构成了我们生活中一幅幅光怪陆离的精彩图案!每天紧锣密鼓的学习结束后,大家回到宿舍的炕上,还要进行一番热火朝天的“学术交流”。我们曾在那个炕上言说志向,憧憬未来。当年睡在一个炕上的10个同学,人人成绩优异,其中6人金榜题名,分别从事教育、医疗卫生等行业,其余4人都成功的经营着自己的公司、幼儿园、电器维修部等。
家乡一带的乡亲们都说:卢庄(我的家乡)的炕是人才的培养基地。更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睡在一个炕上的同学们,那亲密无间的零距离接触,也让我们建立了永不褪色的手足之情!

如今,随着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和卫生条件的提高,土炕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许再过几十年,我们的后代就已经不知道炕为何物了罢!
房是家的标志,炕是家的核心,我爱家乡,更爱家乡的土炕!



